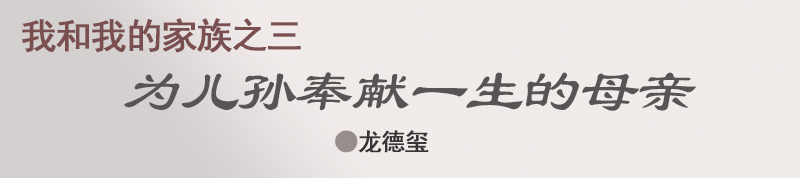◆《我和我的家族》
●前言
●一、龙雨淸家族的发祥地桂花坪
●二、我的父亲和他的商业奇迹
●三、为儿孙奉献一生的母亲
●四、身正能干的德厚二哥
●五、德才兼备的毅远三哥
●六、豪爽侠义的德训四哥
●七、憨厚善良的德芬二姐
●八、厚道精业的德强六哥
●九、聪慧单纯的德芳三妹
我的母亲石增钰,于清末戊申年九月三十日,即公历 1908 年 10 月 24 日,出生在兴文县晏阳镇北门外田湾头徐家,小名徐凤娥。后因外公去世,外婆带着年幼的母亲又嫁到晏阳镇南寿寺旁的新房子石家,母亲便更姓名为石增钰。母亲 14 岁结婚到博望山桂花坪,比父亲小一岁。当时正值民国初期,取消裹脚,母亲的脚裹了不久,便获得解放,留下了裹脚的痕迹,却不是小脚,成了中国特有的裹脚历史变迁的见证,算是幸事。
母亲石增钰像
母亲在 1927 年生德才大姐到 1946 年生德芳三妹, 19 年间养育了八个儿女,平均两年左右生一个,其辛苦程度已可想而知。我们称呼父母和一般家庭不同,叫伯伯、伯娘。而我们八姊妹的排行称号,则更有点复杂。首先是男女分开排行,老大、老五、老八都是女的,我就喊大姐、二姐、三妹。其次是小排行中又插入大排行。我父亲是大房,二姐(老五)出生之后,三婶生了个二儿,便插在我们房,依男排行,定为五,我喊五哥。之后我们搬迁到兴文县城,六哥和我的排行都就依此排下去的。
母亲一生勤劳善良,对我们子女的爱可谓纯朴自然,完全是一种人性的天然。母亲没有读过书,她不识字,没有受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教育。桂花坪龙家,说是地主,其实是以耕读为本的殷实人家。母亲从进了龙家大门的那一天起,就一刻不停地辛劳着。她当媳妇时才 14 岁,相当于我们现在读初二的少女,做饭时要站在一个矮板凳上,才能操作。除了做饭,还要喂猪,拖儿带女。后来搬到县城住,还要帮忙做生意。她是父亲的得力助手,更是父亲的补充。母亲不会说哪些教育人的空话,她只知道关心我们的生活,不让我们受凉受饿受惊,她用她的纯朴的爱来关心我们,用她特有的善良来感染我们。母亲的勤劳和奉献精神,打动了我们每一个子女的心,影响了我们的一生。在这没有刻意教育的环境中,我们七姊妹(大姐 21 岁时病逝)个个都健康成长,个个都事业有成,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最后都有一个美好的晚年归宿。这都是母亲辛劳一辈子的成果,是伟大的母爱所赐。
记得我几岁时,母亲常常背着哥哥、姐姐们,塞一个鸡蛋给我,叫我找一个背静的地方悄悄地吃,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我很得意,以为我是幺儿,母亲对我特别好。可是后来,无意中才发现,母亲对我的这种特殊关照,实际上哥哥姐姐们都享受过,而且对他们说的话和对我说的,都是一样的:“不要让别人知道哈。”后来我才明白,这是母亲的智慧。我们姊妹多,鸡蛋少,只能轮流享受。现在想起来,母亲还挺幽默的。
母亲要求我们都要劳动,做家务活,不听话还要打我们。她的纯朴真是太原始不过了。有时她忙不过来,喊叫我们干活,一点也不温柔,叫二姐为“二鬼”,叫六哥为“六鬼”,我自然就是“七鬼”了。那时我不到十岁,不大懂事,甚至还有点横。有一次,我看到别人穿新衣服,很羡慕,就要求母亲也给我缝一件。母亲说没有钱,我就大哭大闹,竟哭了半天也不消停。母亲终于气愤了,便打我。母亲打我只用巴掌打屁股,一点也不痛,不像父亲生气打人让我们胆战心惊,所以用不着躲避。母亲边打边说“不争气!”这充满悲伤与疲惫的话音,终于触动了我的良心,我的心软了,觉得对不起母亲,停止了嚎哭,不再闹了。虽然那时我还是儿童,但心里也明白,成美商店已失去昔日的繁荣,哪里还有钱给我制衣服,我这不是胡闹是什么?
五十年代初期,是母亲最艰难的时候。那时父亲已去仙峰供销社工作,成美商店的生意奄奄一息,家里有一桌人要吃饭,父亲、二哥、三哥虽然有工作,但都很低,基本上只够他们自己花,无法补贴家里。当时水烟作坊还能勉强做下去,师傅叫石大爷(孤人,后来一直住我们家,直到病逝),四哥、六哥都曾当过他的徒弟,帮着干活。母亲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费用,还想办法做一些另外的小生意,例如推豆腐卖等。我小小年纪也要做家务活,例如下河清洗衣服、和炭巴等,还帮着撕烟叶、推豆腐等。酒厂已停止生产,母亲只好到十多里路远的拖船场去买酒来卖。那天,家里所有比我年龄大的人,都不知哪里去了,母亲便叫我陪他去。我不想去,母亲却执意要我去。没办法,我不得不出这趟差。母亲叫我用竹篼挑了两个能装二十多斤的酒坛,跟着她去。我一边走,一边叽叽咕咕的发牢骚。走出门两百米左右到瓢地沟,我要解小手,把担子放在地上。那是一个倾斜的大石包,石包下是一个陡坎。那酒坛装在竹篼里,上重下轻,我刚把担子放下,酒坛就从竹篼里滚出来,迅速往坎下滚。我眼睁睁地看着酒坛摔个粉粹。我吓傻了,心想这下可惹大祸了,非挨一顿毒打不可。可母亲却没有打我,脸上露出愁苦而无可奈何的神情,大吼一声:“回去!”我于是狼狈不堪地挑着空竹篼跟着母亲回家去了。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件事,母亲一人因承担家庭重担而愁苦的神情就出现在我眼前,勾起我对母亲的阵阵怜爱。我自责我自己,那时我为什么不听话?为什么不去给母亲分担点负担,让母亲高兴一点?
这是母亲 1960 年的留影。
略带愁苦与操心的神情掩盖不住善良的本质,这就是母亲。
我虽然出生于成美商店鼎盛时期,但我多数记忆却是从那些艰难的日子开始的。那时,母亲总是刻薄自己,让我们先吃饱吃好。母亲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,就在灶头上炕一些红苕,等着我回家来吃。我到江安读高中时,母亲把她最好的棉被给了我。她有一床崭新的线织床单,自己不用,也给了我。这床单后来一直伴随我十多年,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。
母亲对我们纯朴自然的爱,影响是那么强烈,以至于我无法抗拒对母亲的感情依赖。儿童时期,每当傍晚,如果母亲不在我身边,无论身处何地,我就感到十分孤寂,想念母亲,像是害病一样,闷闷不乐。我读初一时,县城学生也可住校,我觉得新奇,便住进学校去。可是住进去的第一天,晚自习结束,我回到寝室,看不到母亲,一种莫名的孤寂向我袭来。我无法忍受,便偷偷跑回家去。母亲正在灯下缝补衣服,家里一切如常。母亲没有察觉到我有什么异样,没有问我什么。我在母亲身边默默地呆了一会,觉得没事了,才跑回学校,安心睡了。若干年过去了,这似乎无聊的举动,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,无法磨灭。真的是无聊吗?不,其实这就是母爱的力量。
又有一日,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,我利用晚饭后那短暂的休息时间从学校跑回家去看母亲。找遍家里每一个房间,都不见母亲。我从后门穿过郭家出去,那里连接着一片农田,我才找到母亲。那时正是傍晚,光线暗淡,为了给猪找食物,母亲还在田坎上操劳摘黄豆叶。我喊了一声“伯娘!”母亲才知道我来了。在她抬头看我的那一刻,我突然发现母亲变老了,蓬松的头发中夹杂着白发,憔悴的脸色带着忧伤。一阵悲凉在我心里涌动,说不出的难受。我当时就暗暗对自己说,以后我能找钱了,一定要让母亲好好过日子。 1962 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仙峰教书,第一次领到工资,我立即给母亲寄了 10 元钱去。 1966 年东东出生,我就把母亲从县城接到学校来,一方面让母亲给我们带小孩,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母亲享受天伦之乐,实现我少年时期暗中对母亲的许诺。可是母亲到我那里没几天,校长就向我传达文件,说地主家庭的人不准住在机关学校,要母亲立即回家。我说母亲不是地主分子,不属管制人员。但校长说,还是不能留在学校。没有法,只好送母亲回家。母亲回家那天,学校操场里正在召开斗争阶级敌人的大会,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。我发现,母亲听到这些口号声,神情显得有些紧张。我心里暗暗催促那装载母亲的班车,快快启程吧,别把母亲吓着了。母亲走后不久,我们把东东送回家,让她带。带了两年多,直到东东可以读幼儿园了,我们才把东东接到学校来。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,东东没有生过一次病。每天,母亲或父亲都要去农场为东东买一瓶鲜牛奶,要给东东煮一个鸡蛋,保证东东有足够的营养。后来东东考上北京大学,街房邻居都说,龙大婆(指母亲)带的小孩,真神!这些街坊邻居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德训四哥的大女龙红,德强六哥的大女龙健,都是母亲亲自带过的孙女。龙红夫妇从香港回归起,就一直在香港、非洲、美洲的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,走遍了东西半球,可谓光宗耀祖。龙健却是学霸式的人物,从搞计算机到搞经济,出类拔萃,后来成为顶尖的银行高管。母亲的恩德惠及子孙后代,这难道不是真的吗?
这是母亲 1984 年的留影。那时母亲已的脑梗阻,
但看得出她慈祥的面孔里流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1978 年母亲因脑梗阻瘫痪。我们弟兄姊妹个个对母亲都有深厚的感情,都十分焦虑,立即聚集在她身边。我们在原有基础上,更加完善对母亲的赡养约定,每月都给母亲固定的生活费和零用钱,请保姆照顾她。德训四哥的航天工业部单位还可给母亲报销药费,我们就定时给母亲买药送去。 1981 年我调到兴文中学教书,每个周末我都要带着东东和迎春去看母亲。我有时还去给母亲洗脚。 1983 年东东考上北大,母亲特别高兴,悄悄拿了 10 元钱给东东,就像当年拿鸡蛋给我吃一样神秘。东东也不忘奶奶的恩情,每次假期回家,东东知道奶奶喜欢吃甜食,都要给她买点糖果。 1988 年父亲去世后,母亲送到纳溪和德芬二姐住在一起。 1990 年母亲在纳溪去世,享年 82 岁。母亲和父亲合墓葬于兴文晏阳镇城北苏麻田。
母亲的爱,已转化成我的爱。而母亲的伟大,却成永恒!
1984 年春节四世同堂合影,前排中为母亲和父亲。
( 2020 年 5 月 10 日于成都翡翠家园)